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坐落于阿比多斯尼罗河道以西8英里地方的塞提一世神庙,在古埃及所有神殿遗迹中显得非常独特,不但天花板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连接好几英亩的壁雕也完美无缺。塞提一世为埃及盛世第十九王朝的一位法老,在公元前1306至公元前1290年间统治埃及。
塞提一世最引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生下一个有名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公元前1290~公元前1224年),也就是《圣经·出埃及记》中的那位法老①。不过,塞提一世出国征讨。建立武功,不但建造起几个非常精良的建筑,并非常用心地修复了不少古建筑。他在阿比多斯建的神殿,即取名为“万万年之家”(The Hous,of Millions of Years),在这个属于他的神殿中,祭祖的是“永生之主”欧西里斯。金字塔经文中有这么一段记述:
你已经走了,但是你将会回来。你已经睡了,但你将会醒来。你已经死了,但你将会生还……乘着水。向上游……以神明赋予你圣灵的姿态,漫游阿比多斯②。
早上8点,在这纬度不高的地方,已是天色明亮而万物活跃的时刻了。但当我们进入塞提一世神殿的瞬间,感受到的却是一片寂静与昏暗。除了墙壁上有从地板打上来的微弱电灯光线外,神殿内部大部分仍依法老的建筑家的原始设计,以自然光照明。几条光束从外侧石缝中穿透进来,宛如圣光逼人。光束中灰尘的微粒舞动,和沉重的空气以及支撑着这多柱式建筑屋顶的巨大石柱,成为强烈的对比。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欧西里斯的圣灵,仍然在这里。这不单是想象,也是现实,因为周围的墙壁,占满了美丽而调和的浮雕作品,全都在描绘以散播文明为天职的欧西里斯,如何在死后扮演冥界之王的角色。其中还有一幅浮雕,绘着他即位为冥界之王,而他美丽、神秘的妹妹爱瑟斯则在一旁观看的景象。
我逐一观察墙壁上的浮雕作品,发现欧西里斯在每一幅中戴着的王冠都极为华丽,并各有特色。王冠对古代的法老而言,显然是服装中一个重要部分。至少从浮雕中我得到这样的印象。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多年来如此大规模的挖掘行动中,却从来没有一位考古学者发现过任何王冠,或王冠的碎片,更不用说“开天辟地”的神明所使用的漩涡状仪式用头饰了。
所有王冠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阿提夫(Atef)的王冠。这个王冠形状奇妙,除了有皇家徽纹的蛇形状章(亦即优拉阿斯。墨西哥用的是响尾蛇,而埃及则是用昂头、随时准备出击的眼镜蛇)以外,正中央描绘着上埃及人的白色战斗用盔甲的图案(这个也只有在浮雕中可见,没有实物可供参考)。王冠的两侧看起来是两块如树叶一般的薄金属片,与前面一个机关相连。王冠上面的金属片形成两张波浪形状的刀刃,学者一般认为那象征着一对雄羊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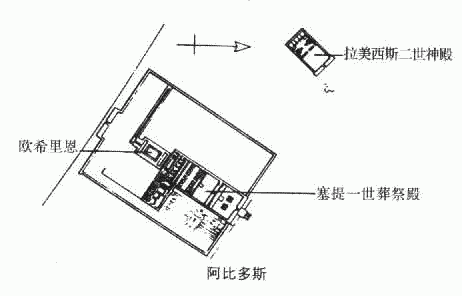
|
塞提一世神殿浮雕作品中,有好几幅是以载着阿提夫王冠的欧西里斯为主题的。王冠看来大约有2英尺高。根据古埃及《亡灵书》的记戴,王冠是雷送给欧西里斯的,“但是,欧西里斯戴上的第一天,头部开始剧痛,雷晚上回来时,发现欧西里斯的头因为戴王冠的关系而肿胀。雷为他取脓。”③。
古埃及《灵亡书》只是平铺直叙地讲出一个故事。但我们不妨仔细想一想:一个会发出热能,使皮肤发炎、出脓的王冠,会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走进黑暗,一直到路尽头的众王之廊(Gallery of the Kings),也就是从神殿入口进去200英尺的多柱式大厅东侧的通道。
通过众王之廊,就好像通过时间之廊一样。在我的左侧墙壁上,雕着的是古埃及120名神抵的称谓和他们主要的管辖圣地。在我右手边,则有一块10英尺乘6英尺大的地方,刻着塞提一世以前的76位法老的名字,而且每个名字都以象形文字,刻在一个个椭圆形的徽纹记号中。
这个图像的文献,就是一般所称的“阿比多斯国王名单”(Abydos Kings List)。金光闪闪的这个雕刻名单,文字从左向右排列,将所有名字以纵向五段与横向三段的区隔,记录下从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的第一位法老美尼斯后1700年,所有法老的名字。名单上最后的一个法老的名字,即为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统治埃及的塞提。在名单的最左边,浮雕着两个人物,一个是塞提,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拉美西斯二世。
在历史价值上与杜林纸草及巴勒摩石不相上下的“阿比多斯国王名单”,对埃及王室的传承做了明白的交代。而这份传承史料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悠远的过去、诸神共同统治的“开天辟地”时期的信仰。所有的神明都以欧西里斯为中心。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紧接着众王之廊后面的,是一条直达神殿后方,并进入另一座与欧西里斯相关建筑的通路。这座宏伟而美丽的殿堂“欧希里恩”,从埃及有文字历史以来,便因与欧西里斯有关联而闻名于世。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保(公元前1世纪曾造访阿比多斯)形容它为:“用坚硬的石头建造起的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建筑……在很深的地方,有一口泉水。要进去时,要先经过一个用巨石做成、做工精致、宏伟惊人的圆形屋顶建筑。里面建造了一条运河,从尼罗河引水……”
史特拉保造访后几百年,古埃及的宗教信仰逐渐被另外一个新兴宗教——基督教——所取代,河川的淤泥和沙漠的细沙,一寸一寸、一点一点地流入这充满传奇性的欧希里恩,终于将它的石柱以及入口上面的横石完全掩埋起来,消失于众人的眼前,同时也消失于大家的记忆中。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弗林德·培崔和玛格丽特·穆瑞(Margaret Murray),在此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考古挖掘活动。1903年,他们发现在塞提一世神殿西南方200英尺的沙漠中,有一座大厅和一条通道,从建筑形式来判断,应该为第十九王朝的作品。不过,在塞提一世神殿的后侧和新发现的厅之间,两位考古学家判断,绝对还有另外一个“大型地下建筑物”被埋藏在地底,而此“地下室”(hypogeum),穆瑞写道:“培崔教授显然认为,就是史特拉保提到的水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史特拉保之泉(Strabo’s Well)。”弗林德·培崔和穆瑞猜测的不错。但是,因为他们资金有限,无法继续挖掘,工作到中途便停顿了。一直到1912至1913年,才有另一位纳维尔(Naville)教授,在埃及古物挖掘基金(Egypt Exploration Fund)的支持下,有机会证实弗林德·培崔和穆瑞的假设。纳维尔教授发现了一间狭长的房间,东北向的尽头,有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及沙岩所建造的入口。
在接下来一季,1913到1914年的挖掘活动中,纳维尔组织了600名当地工人,辛勤地将整个庞大的地下建筑物挖了出来。纳维尔写道:
我们发现的巨形建筑物,大约有100英尺长、60英尺宽,其使用的石块之大,在埃及也应属绝无仅有了。四面墙壁,邻接着17个小房问,每个约仅一个人高,里面没有任何装饰。建筑物本身以三个通廊组合而成,中央一块通廊比两边的两块大。间隔通廊的为两列柱子,每根柱子各由一块完整的花岗岩中切割成形,支撑着一块同样大小的振梁石④。
纳维尔惊异、详实地记录,他如何测量建筑物北侧通廊的石块,并发现每块竟然近25英尺之长。更令他惊讶的是,从墙壁伸出的小房间,地上并没有地板,而挖开地面往下挖时,竟然发现下面的土壤非常潮湿:
小室仅以宽2至3英尺的平台相接。房间另外一端的中央,另外还有一块平台,而房间里面没有铺设任何地板。当我们往下挖掘至12英尺深处时,开始有水渗入。即使后方入口处也没有地板。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推测,过去这里盈满着水,进出小室必须利用小船。
水,水,到处都是水。1914年纳维尔教授和他的工作人员开始大规模挖掘行动时,发现横躺在那个大洞穴下面的秘密建筑物欧希里恩的核心,似乎就是水。欧希里恩正确的位置是在塞提一世神殿地板水平面下50英尺左右的地方,几乎与地下水的水面同高。现在,我们可从东南方一座现代人制作的阶梯走下去。我沿着这楼梯下去,先经过了纳维尔和史特拉保都描述过的入口巨大横楣石,再穿过一条狭窄的木造桥,来到了一个沙岩平台。
平台大约宽40英尺、长80英尺,是用巨大的铺道石建造而成的,周围被水包围。以平台中央为轴,旁边有两座大游泳池,一座长方形,一座正方形。在轴的尾端,另外还有一座楼梯往下,可到达水面下12英尺的深处。另外,平台同时还支撑着纳维尔报告中也提到的两大住廊。每个柱廊都由5根粗短的粉红色花岗岩支柱组成,而每根支柱高约12英尺,四面宽度均为8英尺,重则达100吨。这些巨大的柱子上面,还有花岗岩的横石,显然整座建筑物,过去不仅曾覆盖在大型的屋顶之下,可能还曾使用更大的横楣石。
要了解欧希里恩的构造,必须能够在心中将自己拉至高处,俯视它。由于当时的屋顶已经不见,因此在心中描绘整体构造的工作就更容易了。而且由于建筑物中的游泳池、小室的运河等现在都盛满了水,一直满溢至离平台只有几寸的地方,显然很接近原始设计的模样,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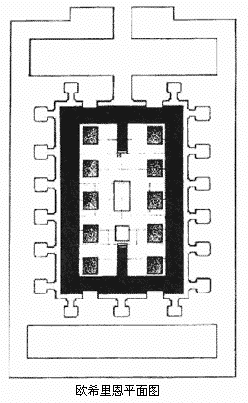
|
以这个方式往下看,我们立刻可以了解,平台是一个四周被宽约10英尺的壕沟所包围的四角形岛⑤。壕沟的四面,则被厚达20英尺的墙壁所包围。这些用红色沙岩堆积而成的巨墙,呈现着多角形的拼图花样。通过厚墙上的开口,我们便可进入纳维尔报告中所描述的17间小室:东面6间、西面6间,南面2间,北面3间。北面3间的中央1间,房间的内侧,连接着1间长方形的大厅,上面还有一部分石灰岩的屋顶。南面也有1间类似的长方形大厅,但是已经没有屋顶了。整个建筑构造的外面,有一圈石灰岩的外壁,使得整体的构造,从外往内,连成墙、墙、壕沟、平台的顺序。
欧希里恩另外一个令人感到好奇的地方,是它的方位不但不正,而且反倒像墨西哥的泰奥提华坎古城的亡灵之路(Way of the Dead),是向着稍微偏东的正北方。由于埃及古文明向来在方位上相当精确,因此我不得不怀疑,这个偏僻的方位绝非偶然。相隔不到50英尺外的塞提一世神殿便完全照准着欧希里恩的方位,可见这背后,必定有一个特殊的理由。问题是神殿与欧希里恩哪个年代更久远?是神殿比照欧希里恩的方位,还是欧希里恩比照着神殿的方位而建的?这个问题,现在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是过去还曾引起过一场极大的争论。20世纪初,讨论狮身人面像及河岸神殿的建造年代时,曾经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主张欧希里恩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1914年3月伦敦的《时代》(Times)上,刊登过纳维尔教授的简介:
欧希里恩引发几项重要的疑问。首先就是它的建造年代。由于这座建筑物与狮身人面像神殿(亦即河岸神殿当时的名称)极为相似,两者均为巨石建造,没有装饰,表露出当时建筑的特征无遗。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欧希里恩和狮身人面像一样,应属于埃及最古老的石造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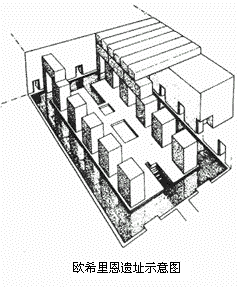
|
自称完全震慑于这座建筑物中央大厅的“壮丽与彻底的单纯”,并且由衷佩服那些“从远方搬运巨石而来并堆积成建筑物的古代人”的纳维尔,在欧希里恩的功能方面,认为:“显然这个巨大的建筑构造,是为尼罗河水漫溢期间而建造的蓄水池……应该是建筑史初期的作品,既不是神殿,也不是坟墓,而是巨大的水池,一个给水设备。这一点,令人极感兴趣……”
的确令人感到有趣,并且想要更进一步调查。纳维尔本想在下一个调查季接着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可惜战争爆发,连续几年都无法在埃及从事考古活动。一直到1925年,埃及考古基金会才重新组织考古调查队,但是新的队长不是纳维尔,而是一位年轻的古埃及学者亨利·法兰克佛(Henry Frankfort)。
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前古典太古时代(Preclassic Antiqui ty)专家而名噪一时的法兰克佛教授,接下这个考古任务后,从1925至1930年,连续主持了好几季的欧希里恩考古活动,彻底地挖掘、调查了该地的古迹,并就他所知的,找到了足够的证据,“确定了建筑物的建造年代”。他找到的证据主要有:
①中央大厅主要入口处南端的上方,有一个花岗岩的鸠尾榫(dovetail),上面雕刻有塞提一世的徽纹记号。
②中央大厅的东面墙壁的内侧,有类似的鸠尾榫。
③北侧长方形房间的屋顶上,有一幅描写天文光景的图画,和一些塞提一世的碑文浮雕。
④南侧的长方形房间中,也有描绘着类似风光的浮雕。
⑤在入口通路上发现了一块石灰岩的破片,上面刻着“塞提侍奉欧西里斯”。
读者或许还记得列明集体自杀(lemming behavior,老鼠繁殖到达顶点后,便往海洋方向移动,大量溺死的行为)之类的社会行为。学者对于狮身人面像和河岸神殿的年代问题,也发生过向相反方向大移动的集体自杀行为(原因只因为发现了几个石像,和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法兰克佛在阿比多斯的发现,也造成了学界对欧希里恩的年代问题上,有180度态度大转变。1914年,学者还口口声声说欧希里恩是“埃及最古老的石造建筑”,到1933年时,他们却突然转而相信那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塞提一世统治时代的一座死者纪念碑了。
然后又经过了10年,古埃及学的教科书已普遍认定欧希里恩的建筑为塞提一世的丰功伟绩,而且写的就好像那是经验与观察而得到的史实,而非一种观测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它不但不是史实,而且只是法兰克佛基于他发现的物证,而发表出来的个人见解罢了。
对于欧希里恩,我们惟一能确定的便是一些塞提一世的碑文及装饰品的出土物,而可以让我们与人物、年代等连结的就只有这些了。从这些文物与塞提一世之间的关联,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欧希里恩为塞提一世所建造的。法兰克佛便是如此主张。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那便是由于出土的装饰品其实相当的破旧寒碜,而碑文上的徽纹记号也并不丰富,或许这些并非存在于这些原始建筑时,而是在修缮、复原它的时候加在其上的(也就是说,采信纳维尔和一些其他学者的建议,欧希里恩是在塞提以前的年代所建的)。
也就是说,关于欧希里恩的起源,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抵触的假设:(A)它是埃及最古老的建筑物,(B)它是新王朝时代的作品。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假设分别有哪些优劣之处。
现代古埃及学者接受的为(B)假设,认定欧希里恩是塞提一世所建立的死者纪念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讨,会发现碑文、徽纹记号等均属间接证据,不但不能证明什么,有的甚至会与法兰克佛的见解互相矛盾。例如,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灰岩破片中,我们发现“塞提侍奉欧西里斯”的字样。这不像对一位原始建造者的赞美,倒像是对修复者的赞美,赞美塞提一世修复,甚至增筑了“开天辟地”的神祗时代所有的太古建筑。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其实相当棘手,也被学者忽略了。那便是被发现有塞提一世装饰及碑文的两间南北向的“扁长室”(transverse chambers)的位置,是在欧希里恩20英尺的厚壁之外。在厚壁之内的巨石建筑物中,并无任何的装饰。这使得纳维尔合理地提出怀疑(法兰克佛却有意忽略),认为后来的两间扁长室与建筑本体并不属于同一的年代,房间可能是在建筑本体完成后经过许多年,在塞提一世时代“当他建设他自己的神殿时”才加出来的。
因此,我们认为假设(B)的基础是建立在法兰克佛从少数的出土文物中做的一些不足采信的解释之上。
相对地,假设(A)的欧希里恩的中心建造物是在塞提一世时代以前好几千年便已完成的说法,则是建立在对建筑物样式的观察上。根据纳维尔的观察,欧希里恩和基沙的河岸神殿形式相近,显示两者是出于同一时代,同一个用巨石建筑的时代。同样地,玛格丽特·穆瑞至死仍相信,欧希里恩不是死者的纪念碑,更不可能是塞提的纪念碑。她说:
这座建筑物是为赞美欧西里斯的秘迹而建,在埃及现存的建筑物中极为特别,显然年代非常久远。它使用的大型石块,正是古王朝时代的特征。而且简单的式样,正说明了它来自一个古老的时代。装饰为塞提一世所加上的。塞提用这个方法来主张他对建筑物的所有权。过去很多法老都以放上自己的名字,来主张对以前法老的建筑物的所有。因此,名字的意义并不大。在考证埃及建筑物的年代时,有意义的是建筑物的式样、石工技术的种类、石块切合的方法等,而非上面刻着的国王的名字。
法兰克佛对这一番忠告应该更注意倾听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禁对他所谓的“死者纪念碑”有所困惑,而曾表示过:“我们必须承认,第十九王朝中并无类似的建筑物。”
其实不止第十九王朝。和欧希里恩类似的建筑物,除了河岸神殿和基沙的巨石建造物以外,在漫长的埃及历史中,竟然一座也没有。而河岸神殿等几个所谓老王朝建筑的巨石作品,似乎独树一格,互相有很多的类似点,但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建筑便截然不同,而它们原始的建筑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无人知道。
为什么我们非要将这些建筑物派给法老时代,而不愿意承认它们可能是在史前时代时便已完成的?从狮身人面像、河岸神殿,到现在的欧希里恩,没有一样直接证据,可以断然证明它们是由谁建起来的。仅凭着一些模糊假设和少数的证物,我们便硬将这些建筑与某个特定的法老(如卡夫拉、塞提一世)拉在一起。除了徒增这些建筑物的神秘性外,有什么好处?那些少数的证物,难道不会仅为后来的法老,在修复古老的建筑物时,为与古老时代建立连结,而故意遗留下来的物品?
离开阿比多斯之前,我还想去确认一样谜题。那谜题被埋没在离欧希里恩西北1公里左右的沙漠中,被滚滚黄沙包围的古代坟场之下。
坟场的大部分坟墓属于王朝时代初期,或更久以前时代的统治者,胡狼之神阿奴比斯和乌普奥特统治时代的文物。身为开道者、灵魂的守护者的胡狼,一直是很多神秘故事的主角。阿比多斯每年都以阿奴比斯的神话故事为蓝图,演出祭神仪式,而且这仪式显然从有古埃及历史以来便已存在。
阿奴比斯守护的似乎不止亡灵,还有更多的谜题,而欧希里恩便是最大的不解之谜之一。难道学者们不该做更深入、详细的调查?学者的任务难道不就是要解开这类的谜题?沙漠中埋藏着12只船首高耸的航海船,难道不是一个大家都急切想知道答案的谜题吗?
而我要做的正是通过胡狼神的坟场,到埋藏那12艘船只的地方,一探究竟。
英国卫报(Guardian),1991年12月21日:尼罗河深处发现古埃及皇家舰队。一队由美国及埃及考古学家所组合的探险队,最近在离尼罗河岸8英里的阿比多斯地方,发现了12艘古埃及木船……根据专家表示,每艘船大约长50至60英尺,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是现在所找到的埃及最古老的船只……专家还说这些9月份便发现的船只,可能是为陪葬法老,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到远方旅行而造的。“我们从来没想到会发现这种船队,尤其在离尼罗河这么远的地方。”探险队长,同时也为宾川大学博物馆埃及文物组长的大卫·欧康诺(David O’Connor)说……
舰队被埋藏于一个由泥砖围起来的庇荫中,而这一块地方则被认为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统治埃及的第二王朝法老卡色卡汉维(Khasekhemwy)的葬祭殿(mortuary templ)。不过,欧康诺却很有把握地认为那些船只和卡色卡汉维没有直接关系,而与附近(而且大都崩坏)的“第一王朝初期的法老德贺(Dier)的王墓有关。船墓不像比王墓更为古老,有可能就为德贺王所建,不过还需要经过证明”。
沙漠突然吹过一阵强风,细沙满天飞舞。为了避风,我躲到卡色卡汉维王殿堂的围篱墙壁下。这里与宾州大学的探险队重新将船只埋入的地点(他们在正当的防护理由下,再度将船只埋回地下)已非常接近。1991年偶然发现那船队以后,考古学家们原本希望1992年能够回来继续挖掘,但是在许多事情的拖累下,一直到1993年的现在,他们还没有重新回来的计划。
在我做研究的过程中,欧康诺曾经寄给我他1991年正式的挖掘报告,中间提到那些船只其实可能长达72英尺⑥。他同时还提到,埋葬这些船只的船形砖墓,在早期的王朝时代,很可能是在地上,一个个挺立于沙漠中。在全新的时候,那种砖墙林立的景象,必定相当壮观:
每个坟墓,原始时候,必定都抹有厚厚的泥土,并涂上白色外装,因此,视觉上就好像12艘(或更多)巨大的船只“停泊”在沙漠上,在埃及灿烂的太阳光下,大放光芒。这些船只处于停泊状态的意识强烈,在数个坟墓的船首和船尾下,发现有形状不统一的玉石。这些玉石不可能是偶然或天生,而必须是有意摆放在那里的。从位置来看,玉石也一定是故意,而不是无意放置着的。我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帮助船停泊的“锚”。
正如同基沙的大金字塔旁地下发现的140英尺航海船(见本书第33章),从阿比多斯的船只构造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足以应付大洋上任何恶劣的天候和激荡的波浪。得克萨斯州A&M大学的航海考古学家雪儿·海丹(Cheryl Haldane)认为这些船只的设计精良,“使用高度的技术,而船姿优美更不在话下”。因此,和大金字塔的船一样的是(不过至少要更古老500年),阿比多斯船队似乎很明白地显示,埃及人在3000年悠久历史的最初期,便已积蓄有丰富的航海传统。而从早在埋藏阿比多斯船只的1500年以前(也就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在尼罗河谷中发现的最早的埃及壁画中,我们便已看到了流线型高性能的大船在水上航行⑦。
是否有可能,早在有正式文字历史前的公元前3000年,便有一支具备丰富航海经验的人们,来到尼罗河谷,并与当地的土著住民有了接触?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便不难解释从埃及沙漠中发现船只这种重复出现、无法解释的怪现象了(金字塔经文中也描写到非常复杂的船只构造,有的长度更达2000英尺)。
在提出这些疑问的同时,我还怀疑船只在古埃及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很多学者都先后指出过,船只是为了载运法老的灵魂而建造的。不过,我觉得,象征意义并不能够解答为什么埋藏于地下的船只,是以如此高度的技术水准制造而成的。这种高超的设计与制作技术,必须是有多年的经验发展出来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探究一下——就算为了否定有这种可能——基沙和阿比多斯的船只,不是由那些热爱自己土地,在河边定居,从事农业的古埃及人所制造出来,而是出自于另外一批更高等的、有航海文化的人手中?
既然有高度的航海文化,这批人必定知道如何从星象的观察探知方位,并且为能航行远洋,而发展出制作地图的技术。
是否有可能,这个文化,同时也精于建筑与石工,专门制作以多角形的巨石盖起如河岸神殿、欧希里恩之类的建筑物?
而且,有没有可能,这些人与“开天辟地”创始万物的神明们,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不但带给埃及人文明、建筑、天文、算术与文学的知识,而且还传给他们许多实用的技术,包括埃及人受惠最深的农业。
我们从各种迹象中发现,尼罗河谷在北半球冰河期的末尾曾经有过农业文明,以大规模的农业栽培实验,创造了地方的“飞跃”性发展。然而,从它飞跃的特质来看,这个农业文明不是由本土发展出,而只有可能是经外来、不知名的思考的引介,才得以发展出来的。
注释
①日期出自《古埃及地图》(Atlus of Ancient Egypt)。有关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出走的资料,见奇臣《胜利的法王:拉美西斯二世生平》,70~71页。K.A.Kitchen,Pharaoh Triumphant:The Life and Times of Ramesses Ⅱ,Aris and Phillips,Warminster,1982,p.70~71.
②《古埃及金字塔经文》,285、253页。
③古埃及《亡灵书》,175章,引用于《古埃及神话及象征》(Myth and Symbol in Ancient Egypt),页三七。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trans.R.O.Farlkner),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89.
④伦敦《泰晤士报》,1914年3月17日。
⑤纳维尔《阿比多斯考古挖掘活动:欧西里斯的水池及坟墓》,第1卷,1914年,160页。E.Naville,Excavations at Abydos:The Great Pool and the Tomb of Osiris,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Volume Ⅰ 1914,p.160.
⑥以传真直接送给笔都,1993年1月27日。
⑦《古埃及金字塔经文》,192页:“噢,晨星,荷拉斯,你有一个灵魂,你出现在770求比特大的大船上……请带我到你船只的舱内。”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